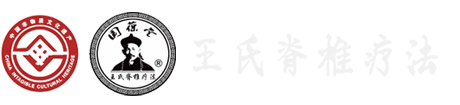对话王兴治(十)当初就没想继承祖业
本 期 导 读
我们家这个竹罐,跟现在好多人所理解的拔火罐不太一样,它集拔罐、刺络放血、药物熏蒸于一身。
田 原: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主任
著名中医文化传播人
王兴治:国葆堂清宫王氏脊椎疗法继承人
沈 生:策划人,摄影师
其 他:刘医师、常医师、就诊病人等
——北京国葆堂《对话王兴治》
田原:你是地道的北京人?
王兴治:也谈不上地道,以前也不一定是北京的,但我不是满族,是汉族人。我还记得当时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家族认证的时候,专家问我,你是满族还是汉族?我说我们是汉族。人家专家说,这就对了,(清朝)御医一个满族人都没有,都是汉族。谁如果祖上是御医,还是满族人,那就连理都甭理,肯定是假的。当时满族的医疗技术比汉族人低多了。
田原:家里有这么个家传的宝贝,当初为什么没有学医?
王兴治:说实话,传到我这代的时候,开始我就没想过做这一行。我呢,本来是中文系的,又学了个无线电专业,我们二三十岁的时候,不是我想干嘛就干嘛,是党叫干啥就干啥。我刚工作的时候在电子部做音响师。那时候也是刚改革开放,咱们心里都是那么点儿崇洋的念头,中医都已经不太时兴了。
那时候我成天摆弄的都是美国进口的高级仪器,别人一看都花了眼了,上百多个钮,普通人都不知道按哪个。我们家这门手艺呢?我从小就看我爷爷做,提溜着破竹罐儿,拎点儿破药,土得都掉渣儿。跟人家外国人那设备没法比。而且我当时在音响界已经很有名气了。过去公主坟儿那个音乐喷泉,就是我做的。国务院以前发音响工程师证,现在这个证已经不发了。有这个证的,活着的可能不超过十人,我就是其中一个。
其实我爸早就想让我接这摊儿,但我当时不想接,我爷爷也好,我爸爸也好,都觉得这门儿技术是家里几百年来传承下来的一个非常好的宝贝,可是我开始并没觉得它是个宝贝。因为我有自己的事业,而且可以说我的事业做得还很成功,有所成就。
田原:什么原因让你改变了想法,回来继承家传的祖业?
王兴治:有一个偶然的机会,几个局级干部来拔罐,我爹让我在一旁帮忙。他们在治疗的过程中说,我曾经在哪个医院治过,都让做手术。但是我爹给他们治好了,也不用做手术了,我原来不知道,我才发现,原来别人都治不了这些个病,原来这个竹罐确实是宝贝,是好东西。它确实有疗效啊,不是我一个人说,是每一个做过治疗的人都能感觉得到。
田原:有些人做医生并不是他一开始的追求。我一直觉得一个好医生是被命运指派的。所以这样的人就有使命感。
王兴治:有使命感。有时候我觉得我就是这样一个人。比较信命,现在国家重视中医药,越来越多的民间中医绝学、绝技被收纳进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,有了这么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,我要把老祖宗的文化和绝技好好传承和发扬下去。
我这个人啊,做事信心坚定,做什么都专一。决定做这行的那一天,我就把那么大的洋设备都给扔了,专心致志地来做这个,我以前学中文出身,读中西医方面关于颈腰椎治疗的书,我没问题。我看的书很多,中医的,西医的我都看,他们对这一类病的看法和治疗手段,我都要烂熟于心。如果连基本的理论都不了解,肯定做不好啊。
田原:去年,吴少祯社长跟我提到你这儿的时候,真是透着关切。一直以来,中医的原生态越来越珍贵,对于民间或者宫廷医学来说,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不是很理想。
王兴治:很不容易。我过去在医院里边儿,也就能够“坚持”一年,做不长。为什么?刚开始在一家西医院,院里很高兴,有一个治颈椎的好方法,能树立一个品牌。一年以后,院长找了我,说兴治你得走了。我说为什么走啊?他说不是你不行,你要再待下去,我这院长干不成了。为什么呀?每年我这儿五六百例手术,今年不到一百例啊。你说我少挣多少钱啊?
后来换中医院吧,它不做手术啊,去了以后,一开始医院也很看重,引进了一个新技术,老百姓都说好。到了一年,又待不了。我在那儿,按摩科和针灸科的病人见少了,别的科拔罐的更不成。
王氏脊椎疗法成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后,市文化局、区里以及非遗办的有关领导都大力支持,多次进行项目的实地考察,并划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补助经费,解决我们的实际困难。今天虽然取得了一点成绩,与市、区有关领导的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,我只是做了一点实际工作,很感谢他们。
田原:老百姓是务实的,他不管你什么理不理论,什么大医院,治好病才可信,而且现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,这也是疗法与非遗的强强联合了。
王兴治:区委和区政府都很重视这件事,区长、书记们就来视察指导过。北京电视台的《这里是北京》栏目也给我们做过报道。
田原:做几个疗程能痊愈?
王兴治:一个颈椎病在我这儿,三到四个疗程基本搞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