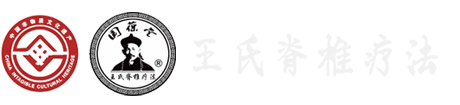竹罐医生王兴治
颈椎病、腰椎病早已成为了都市人的常见病,目前世界上医疗界对颈椎腰椎病的认识,一般情况下会通过一些保守治疗的方法来缓解疼痛,严重时则必须手术,而手术却伴随一定的风险,但在2011年,国家公布的国家级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-传统医药项目中有一项为“王氏脊椎疗法”的中医诊法,却可以通过保守治疗治愈颈腰椎疾病,这种疗法的传承人正是本期大时代人物的受访者王兴治。
在王兴治的治疗室里,只看见患者们趴作一排,大夫用玻璃弹针在脊椎周围的穴位上弹了几下,刺破皮肤,眼看着就有血珠冒出来了,身旁的大药锅里取出来的小竹罐,一个个吸附在针眼上,不一会儿患者的脊椎两侧都密密麻麻吸附着二十多个小竹罐,这些小小的竹罐到底是怎样的原理,仅仅通过在皮肤表面的吸附就能解决身体内部骨骼的疾病?
——“有一个飞行员,开飞机的来治疗,他说你通过什么来把我这个病治好,我想了半天不好跟他解释,我就说,这么说吧,一个轰炸机五个发动机,同时使五个发动机同时出现故障,这是什么原因,这飞行员对这个可熟,他说一个是没油了,一个是油路堵了,我说这就对了,我说五个发动机是什么?肌肉、骨骼、韧带、神经、筋膜,就是您这个病是这五个方面出了问题,那么您心脏在跳,说明油没断,是哪儿,油路堵塞了。那我就通过王家的这个罐、针、药,把你堵在管里的东西给它清出来,让它循环起来,给它这个五个发动机给上营养,自然就好了。”
王氏脊椎疗法一次治疗的时间为15分钟,治疗结束时,医生取下患者身上的小竹罐,并将竹罐拔出的废物倒出,这些红色的各种形状的物质,就是人体内的浊和痰,通过这些浊和痰的形状和颜色,医生能快速的判定患者的恢复程度。
——“一开始都是小月牙小月牙小月牙的,那就不通了,慢慢等通了以后,它就出来那个像毛毛虫似的那么长一根一根的,那就快好了,基本上色彩也变了,变得比较鲜艳了,所以就通过它的粘稠度、色彩、形状,就能确定他的病目前好的程度,这个我们祖先这四百年的历史了,都是一辈一辈传下来,什么样的就什么状态了。”
——“这本就是咱们家留下来的,同仁堂给咱们家的药目,实际上这个方子只有御医才有。”
王兴治的王氏脊椎疗法,是家族一脉相承,王兴治的祖辈曾经有两人担任过清朝宫廷御医,最早的一代可以追溯到顺治时期。
——“祖上王汝清是治疗二毒,什么叫二毒啊,内毒和外毒,什么是外毒,蚊虫叮咬毒蛇咬伤,内毒呢,什么疖子 瘤子,这是内毒,开始的时候是清军在打仗,就是和明军在打仗,明军已经知道那箭上要弄点毒,毒箭一射上,沾上你就差不多就死了,这时候对清军的困扰特别大,最大的就是屡屡的大将就丧失了,当时就急征我们祖上王汝清进入军中,在打仗过程中,就是还没打这个仗呢,这个药锅就煮上了,这罐就在那儿准备着,当清朝的将军们中箭了,赶紧抬回来把箭拔下来,跟着就一个一个拔,就反复的把这个毒液就拔出来,这时候就大大的减少了清军的死亡率,等到战事平定以后,顺理成章的也就进了宫里了。当时说再治毒箭伤,恐怕也没有什么毒箭伤可治了,我祖上就开始考虑,我们家同时能治内毒,实际上我们认为颈腰椎病也是内毒所致,就是你像痰和浊,在我们认为就是内毒,所以就开始进行腰椎颈椎 膝关节这一类的治疗。”
俗话说“伴君如伴虎”,稍不小心就要人头落地,于是王兴治的祖辈王汝清就坚决不想让自己的儿孙再入宫当御医,但无奈的是,王氏脊椎疗法的名气太大,到了乾隆年间,王氏脊椎疗法的第四代传人王昭恩又被招入清宫,当起了御医,至今在第一历史档案馆里,还保留着王昭恩为十一福晋治疗的档案。
大宅门是一部脍炙人口的电视剧,说的是百年医药世家老白家的故事,其中有一个情节,在七七卢沟桥事变后,日军侵占北平,逼着老白家交出祖传秘方,而王兴治的家族也有过相同的经历。
——“日本人打到北京以后,当时有一个协会,这个协会是乐家在掌着这个协会,乐家就是同仁堂,那么当时呢,日本人就把这个协会就要求他们献出秘方药方,都得交给日本人,完了后来我爷爷呢,就找到当时的会长了,就是老乐家,说你看这事怎么弄,老乐家说我这儿就得跟他扛,因为我药店 药铺 厂子都设在这儿,一时我是走不了的,你们老王家可以啊,你们老王家就是点管药,你折吧折吧走了就完了,他找不着你不就完了吗,这时候我爷爷一听也对啊,带着我爸全家举家跑河北了,直到解放以后又回到北京。”
新中国成立后,王家为什么没有选择继续行医,当父亲提出继承,王兴治从断然拒绝到接受,这中间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?
新中国成立以后,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,中国政府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,通过合作社或公私合营的形式,改造为集体或国有经济,王兴治的爷爷考虑到如果一旦和公家合作,祖传医术就不能只归王家所有,再加上对祖辈前清御医身份的担忧,所以王家没有用祖传医术来谋生,王兴治的父亲当了一名园林工人,而爷爷则赋闲在家,祖传的医术仅限于用来帮亲朋好友治疗。1953年王兴治出生之后,由于父母工作很忙,王兴治就一直跟着爷爷,而幼年跟随爷爷治病的经历,就成为了王兴治继承祖传医术的启蒙。
——“就是他看着我,给别人看病,一边带着我,到人那儿,人家看着我,他给别人治治完了 他给我领走,就这么一过程,也就是我爸给别人治病,也是看着,也是耳濡目染的。”
1968年12月,毛主席下达了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”的指示,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,当年在校初中高中生全部迁往农村,而这时王兴治正好初中毕业,他被分配到内蒙古插队,在此期间,爷爷已经去世,父亲成为了王氏脊椎疗法的第十二代传人。
进入七十年代之后,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等各种名义逐步返回城市,直到1975年,王兴治才回到北京,被分配到国营797工厂工作。
——“应该说我在797厂那工作,成绩还是不小的,在这个阶段当中,我读了大学的中文预科班,同时我红旗夜大中文系毕业,上了五年,再有一个我到工程部以后,我的业绩应该也是不错的,亚运会比如丰台体育中心之类的,我当时做完了丰台工程,设备是匈牙利的,匈牙利还给我开了一次招待会,说感谢797厂,以神奇的速度出色的跟他们完成了合作。”
随着王兴治的事业蒸蒸日上,父亲的年纪也越来越大,父亲不想看到祖传了三百多年的医术后继无人,于是劝说王兴治跟着自己学习家传的脊椎疗法,但那时的王兴治对祖传的这门医术,根本就瞧不上。
——“那个罐 针,土了乌叽的一看,那在电子部工作,那都是机器设备那东西一看,很复杂东西洋机器,一看我干的那么先进,我就没想着做家里的那些事。”
从头再来,这熟悉的旋律,曾经伴随着一部分中国人,度过了那一段十分艰难的时期,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加快改革步伐,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,下岗浪潮波及全国大多数国有企业,王兴治所在的797厂也受到影响,他成为了下岗队伍中的一员,但是这个对大多数家庭来说非常沉重的事情,却让王兴治的父亲非常高兴。
——“那会儿已经改革了,可以自己干点什么了,我父亲说你跟我干吧,主要的当时就想帮我父亲做个帮手,他到哪儿去治疗呢我帮他,比如说他扎针我帮他起起罐,好多来的名人 专家 什么领导 说这是某某大医院根本就治不好,结果在我一看,我父亲在治疗过程中 好了。慢慢的 我就对这个了解了,我没想到家里这个,祖先留下的这么神奇,所以呢我就慢慢的开始热爱家里传下来的工作,从那我就开始下决心,这辈子后半生就做这个。”
王兴治发现,祖传医术存在很多弊端,于是提出了改革,他究竟做了哪些改革呢?父亲对这些改变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?
从亲眼见证家传医术的神奇,到亲手为患者治疗,王兴治越来越觉得,自家的疗法是个宝贝,既然是宝贝就不能仅仅只为少数人服务,应该让更多的颈腰椎患者得到更好的治疗。于是王兴治向父亲提出了改革,而改革的第一项却是收费。
——“我爹呢就是给别人治病,就是朋友治病,不要钱。大概在2000年的时候,我就跟我爸说 我说你必须收钱,不收钱就没有发展,那么我想把它做好服务于更多的人群,这就是我的目的,那么首先你不得不从商业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,如果不从商业角度考虑问题,那就说资金链如果要断了的话,别说发展了,自己就会死掉。”
既然要收费,就要让患者感觉祖传医术安全可靠,而父亲所使用的玻璃针和竹罐,都是几个人甚至十几个人用一套,这样很容易造成交叉感染,不符合现代医疗最起码的卫生要求,这就成为王兴治迫切要解决的问题。
——“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必须和法律不能发生冲突,卫生部有一个沾血制品一次性,那首先不把沾血制品弄成一次性,那么我们这个疗法就是再好,它的风险是极大的,我说爸能不能把这个针改成一次性的,我爸说 那,难。我说为什么,他说我拿着玻璃划一上午,划出几百个,从那里挑来挑去,他说符合我们家这个就是做治疗的针的长度的针,只能挑出两三个。我在工厂干过,我知道什么都得靠模具,那我就做一个掰具,把会这个玻璃往里一插,这边拿一个棱,一掰一个一掰一个,那我一上午就能掰几千个,那一检查起码百分之六七十合格,这问题解决了。”
针的一次性问题解决了,王兴治又联系了位于浙江的一个紫竹基地,批量生产竹罐,虽然成本相比以前有很大提高,但王兴治认为要想商业化正规化,是必须付出代价的,而当新的一次性竹罐投入使用时,王兴治却发现了新的问题。
——“您这个削完的这白竹子,削完这个罐是白色的白白的,那我们家的罐经过反复使用颜色已经很深了,有的跟那墨似的那么深,那么通过用这个一次性的罐以后,发现疗效差了,非常差了不是一般的差,这时候我就特别发愁,坐着吃饭的想睡觉的时候也想,一次偶然的机会吃鱼,我发现那个带鱼的鱼刺里头,酱油浸在鱼刺里了,我就问这个带鱼是怎么做的,人说用高压锅做的,脑子一下子就想 如果说把这个药 用药搁到高压锅里,把这竹子浸煮一个小时,我们现在的规范是一小时浸煮,相当于这个竹罐两百次的反复使用,疗效解决了,同时我们还申请了专利,一种可给药的负压器,这种专利申请了,过了一年我们又再申请了医疗器械,到现在我们有正规的医疗器械批文。”
王兴治开始承包医院科室,没有行医执照,难道他是无证行医?就诊患者不多,他又靠什么方法来解决?经营造成连年亏损,他又如何面对父亲的责问?
万事俱备只欠东风,有了祖传医术,有了符合现代医疗要求的治疗器械,王兴治还缺乏一个正规医疗场所,于是王兴治想到了承包医院科室,但是按照国家的规定,个人从事相应的医疗活动,必须取得医师执业证书,那么王兴治在没有证书的情况下,是怎么说服医院进行合作的呢?
——“你比如说,有一辆汽车我会开,那我开出去警察抓住是什么,大家都不用说了,那我请个司机来开这就没问题了嘛,这是开车很正常嘛,实际上当时我就认为我必须得遵守国家的这个对医药的政策,这在申遗的过程中,当时也是议论比较大的,他不是医生怎么就得了非遗了,这是不能进非遗的,当时我就说了非遗是什么 是祖国的一个非文化的一个遗产项目 它不是一个医疗内容 那么在我这儿 我只不过是一个技术的拥有者,我教会了大夫用我们家的方法去检查,我教会了护士用我们家的方法去治疗,那么我自己不做了。”
王兴治的门诊克服种种困难,终于开张了。但是由于王氏脊椎疗法的知名度不大,上门求诊的患者不多,赚的钱不多,而且承包了医院的科室,需要付房租交税,每月还要给聘请的医生护士开工资,在七年里王兴治换了七家医院,不仅没有赚到钱,还亏了八十多万元,这给王兴治带来了不小的精神压力。
05年的一天,偶然乘坐公交车的王兴治 看到一则宣传广告,而这一则广告带给了他新的想法。
——“我坐公交车 我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里头有剪纸 武术 中医药,当时我看到有中医药以后,我猛的一下,我说我们家的这个疗法,为什么不申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啊。”
王兴治认为自家的祖传医术,无论从历史传承还是治疗效果上,都应该够资格评得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。俗话说“千里马上有而伯乐不常有”,王兴治正是在申请国家级非遗项目的过程中,结识了王氏脊椎疗法的伯乐。
——“我就打听到评委,国家级的评委是柳长华教授,就到中国医科院找柳长华,不瞒你说我找他不下十次,完了我告诉他我们这个疗法对于什么什么疾病治疗怎么怎么好,就跟他不断的说,但是不冷不热的那个态度,最后我都没办法了,我老找人家老是这态度,我说这么着,申办区非遗项目我这儿有一个申请的一个小的视频,我说您看看我这个视频,您看如果行呢,我就来,如果不行呢,我就不来找您了,他拿着鼠标就这姿势,把这盘往里一放。咦 这是你们家的,我说是的,全套的,我说全套的,他说这个项目是中国有名的项目,我一直以为已经绝迹了,你们在哪儿,明天我就去。”
——“我在内蒙的一个博物馆里头看过,蒙古人历史上放血的方法,用那个石头,就是那个石头把它掰成尖,绑在一个小木片上,这样来点刺,我就很仔细了解,他还有药物,药物用那个竹罐,用药来煮,然后点刺,就这个拔罐的方法,它比现在的那些普通的拔罐,把那个淤血拔到皮下来,十天半月都消不下去,要强多了。所以说我一看,我说这些东西,它是民间里有着历史渊源的东西。”柳长华说。
随着王氏脊椎疗法入选2011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,王兴治的名气也越来越响,这时已经是王兴治在第八家医院承包科室了,业绩开始好转甚至有了盈利,但却在这时,医院的院长找到王兴治,要求提前终止承包合同。
——“院长来找我了,你赶紧打包走人,我说怎么了,是我干的不好还是怎么回事,他说不是那么回事,你再待下去,我这院长都做不成了。你没来之前,我们每年四五百例手术,今年不到一百例手术,你说我损失多大。那就走呗。”
据估算,2011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市场价值可达到一亿元人民币,有很多人看到了其中蕴含的商机,愿意出大价钱买断王氏脊椎疗法。
——“当时有一个为日本人找我做治疗,做了五六次他觉得好,他告诉我说太好了,完了请我吃饭,他的翻译就告诉我老板准备用六千万把你的技术买了,同时给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股份,咱们可以商量。后来我就问他 你拿这个技术是到日本去,是给日本人做治疗?他说不是,就在中国做,我一想,日本人你拿着我们中国人的技术 来挣中国人的钱。我一口回绝了。”
2012年,王兴治在北京的建国路,开设了现如今的国葆堂,在患者眼中,他是竹罐神医,在徒弟眼中,他是良师,而外界的人则认为他是名利双收的成功人士,面对这些说法 王兴治又是如何给自己定位的呢?
——“说心里话,四十岁左右的时候,刚干的时候可想发财了,说不想发财那是假话,甚至就想什么时候我能有几千万上亿,随着年龄增大就是这个欲望越来越小越来越小,但是对事儿 还是想在有生之年多做点事儿,我什么时候能做到 让大家都受益,这就是我的一个期望。”
经历近四百年岁月,玻璃针 紫竹罐,如今在王兴治的努力下已经绽放出新生命。但对于这样的成绩 王兴治觉得还不够。因为他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,就是希望自己祖传的医术能够帮助更多人,希望更多患者不用再经历手术的痛苦。